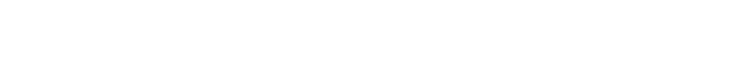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李彦台、匡顺生、孙元凤、王卫、鲜继春、李文亭、冯锦明、孙恩如、柴斌、吕思明、左玉科、刘如愚、尹洪林、李如文14位老同志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10月21日,学校分别在青岛、东营、北京组织看望了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老同志,为他们送去了纪念章,表达学校对老同志的崇敬与关心,感谢老同志保家卫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为学校发展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30多位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老同志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作,他们当中有荣获三级解放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二级国旗勋章的志愿军团级指挥员;有先后参加了上甘岭、反登陆等战役的老战士;有三天没吃没喝,把水让给战友的通信兵;有冒着炮弹横飞为前线运送给养的汽车兵、抢架桥梁的工程兵;有争分夺秒救死扶伤的战地医护人员等。这些老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为保家卫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来校工作后为学校的发展建设付出了自己的辛勤努力。
石大丨历史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历史长河,回顾石大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故事和老战士的事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
以科研支援“抗美援朝”

图丨曹本熹(左)在开展实验研究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1950年又爆发了援朝战争,全国人民都在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献力。北京石油学院的前身清华化工系、石油系,由曹本熹、朱亚杰、侯祥麟、武迟等几位教授负责,率领张履芳、赵铁玲、孙怀琳、徐述华、孙岳明等研究人员,成立了燃料研究室,从事军用油品的研究,培训部队油料工作人员,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些研究人员,后来大都成为我院教工。
志愿军老战士鲍冲

图丨鲍冲教授
在教工队伍中,乃至学生当中,有许多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指战员。石油储运专业的老教授鲍冲,当年就是从志愿军战士转入我校读完大学而留校任教的。
鲍老1948年参军,在以杨得志将军为司令员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俘管团”当干部。他们在向大西北胜利进军的路上,朝鲜战争爆发,兵团立即待命转战“抗美援朝”。1951年2月20日入朝,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1951年4月下旬,该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是役打得非常惨烈,十九兵团共歼敌四千多人。特别是在雪马里地区的进攻战斗中,英军唯一缀有两个帽徽荣誉的“格罗斯特郡团”几乎全团被俘,团长兼直属营营长卡思也成为我军俘虏。鲍冲所在的“俘管团”是专对俘虏进行管教工作的机构,随着俘获“联合国军”人数的增多(最多时达两千多人),工作倍加繁重。在敌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风餐露宿,昼夜不眠,保证俘管任务的完成。时有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安康采访他们“俘管团”,发表管教战俘照片,引国人关注并获得新闻奖项。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局呈现对峙状态,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十九兵团在杨得志指挥下,为促成朝鲜战场的敌人进入防御阶段,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志愿军各部队的俘管机构整合,鲍冲等百余名志愿军奉调回国接受“建设培训”,准备保送这批青年战士转到新中国建设战线。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安排下,1952年春他们离开炮火连天的朝鲜,回到祖国安东市,足足连睡了十多天。休整后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即就被清华大学接到校园。清华大学师生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以隆重的仪式热烈迎接“最可爱的人”入校学习。经几个月的文化补习,1952年9月,已有中学学历的鲍冲以“调干生”身份入清华大学土木系攻读本科。不久又服从组织安排,转入新成立的石油系储运专业学习。1953年,以石油系为基础组建北京石油学院时,这位刚从志愿军转为大学生的鲍冲,随系到我校继续读完石油储运专业。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离休。
“志愿军杨连弟英雄连”的特别排

图丨杨连弟连连长胡占芳来校作报告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凯旋归国,全校一派学习志愿军热潮。炼制系同学开展了学习“志愿军杨连弟英雄连”的活动。杨连弟是志愿军著名的“登高战斗英雄”,烈士所在连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杨连弟连”。1958年,炼制系同学与该英雄连队建立起军民友谊联系,炼56—1班被铁道兵司令部批准命名为“杨连弟连特别排”,英雄连的后任连长、烈士的父亲都到过学院访问、做报告,在同学中播下革命信仰和革命英雄主义种子。
身残志坚的志愿军战士田克东

图丨留下严重烧伤身体的田克东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校长田克东,也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1953年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著名记者金凤写的一篇报道《永远是个不残废的战士》,介绍过田克东的感人故事。 田克东是志愿军150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他在汉城追击战中,一颗凝固汽油弹落在他身边,恶毒的火焰迅速燃烧着他的头、脸和双手,被烧成重伤。随后,辗转回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进院时,他的生命是危险的:眼皮烧去了,眼睛终日不能闭上;嘴唇皮烧去了,嘴唇不能张开,只能用一根小橡皮管送一点水和饮汁进去;耳朵、双手、后脑部和颈部全烧坏了,颈脖不能转动,双手不能伸开。在一年半时间内为他动了十五次手术:摘去左眼球,补上右眼皮,校正倒生的眼毛,把长成球状的双手手骨用小锯锯开,补上嘴唇、外耳,拉下他腿部和腹部的皮肤补在他脸部、后脑部、颈部和手上,已被彻底毁容。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窗外沸腾的生活,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呼唤着他,他的心也在沸腾着,一定争取早日出院工作。他咬住牙,忍住疼痛,用仅有的半截拇指的右手,学会了夹镊子,学会了挂衣服,拉窗帘,开抽屉,学会了夹住铅笔写字,自信“就凭这半截拇指,我还要办大事情哩。” 出院后,根据他本人的请求,上级安排他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任名誉校长。但是他并不仅仅限于“名誉”,还是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经常和学生交谈,做报告,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许多当年的“石油附中”校友,至今还保存着这位满目伤疤的田校长用半截拇指给自己题写的人生箴言和激励上进的话。“文革”迁校后,田克东被转移到山西临汾休养。后回京,2014年10月10日,96岁高龄的他逝世。
从抗日到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单巩

图丨我校单巩少校、孙卓夫大校和何仁江中校(由左至右)
单巩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参加新四军投入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转为解放军作战,从苏北打到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接着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他作为一名指战员战斗在最前线,参加了其中的两个战役。平津解放后,他随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一直打到广西睦南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单巩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前夕于1953年5月回国。在长达十年的战火纷飞的日月里,单巩多次负伤多次荣立战功,由一名少年成长为身经百战的我军团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二级国旗勋章。
1960年,单巩转业到我校,为校党委常委,先后兼任人事处长、保卫处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这位“老新四军”“老解放军”“老志愿军”在我校工作了二十多年,为学校的建设、发展,特别是在“文革”迁校东营后困难的维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石大人不会忘记,1966年他参加领导了“胜利建校”,率八百师生在东营盐碱滩上建造了四万多平米“干打垒”土房,使其后学校被迫迁离北京时,在此有了个落脚点。在“文革”中,他被冤受尽“造反派”批斗之苦仍坚持正义,得到大家尊敬。尤其是在东营办学初期,群众生活非常困苦,他参加领导了创建农场和炼油厂的工作,为稳定教工队伍和改善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单巩奉调山东教育学院任党办、院办主任。1984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2012年元月17日在济南病逝,享年86岁。
刘如愚:抗美援朝,我在1089.6高地上

图丨刘如愚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6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声音时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回荡,让我回忆起我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我不会忘记共产党的威武雄姿,我不会忘记攻打1089.6高地的艰难,我不会忘记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任建民同志。
1953年5月,我在志愿军三十三师通讯连当无线电员。一天,连里命令刘守忠、谭人华和我三人去九九团支援攻打1089.6高地的电台联络工作。我们向鱼隐山进发,到达后在一个猫耳洞里见到我们师通讯科王文杰科长和九九团的通讯股长。我分到一营,不久二营报话小组长杜定保、无线电员唐杰先、一营无线电员任建民三人带了两部两瓦电台到了。杜定保是个老同志,有工作战斗经验,他走在前头,我们从鱼隐山背面向山顶走去。路很小,两边都是虚土,要踩稳,否则踩空了滑下去会往下溜,起不来了。敌人用两挺高射机枪封锁,满山无一棵草,唯一的通道是人们上山下山时,踏出来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年纪小、个子小,身背30多斤重的电台加组合电池,高一脚低一脚大口喘粗气往下奔,又重又累,实在跑不动。跑一阵后,路边有一个能躺半个人大的坑,我就顺势趴下了,只顾大口喘气,也不管那子弹在身边爆炸,休息片刻,爬起身子来继续往前跑,眼看不到百米就到八号坑道了,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光秃的石梁,又是急转弯,我没控制住脚步,一脚踩空,人顺着浮土往下滑,好在滑下去不足一米就停住了,杜定保在前面喊我赶快跑过去。再往前八号坑道口有人喊“那人死了!那人死了。”敌人以为我必死无疑,把枪口转了过去。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手脚把浮土踏实,一使劲就蹿上来了,敌人机枪再打过来时,我已经进入安全地带,随后任建民、唐杰先也来了。任建民说装联络文件及用品的文件袋丢了,就丢在我刚才掉下去的上方。唐杰先一听马上返回找到文件袋又跑回来,我们四人顺着残缺的交通壕跑步进入八号坑道。
八号坑道有三个口,我们进来的是北口,东口炸塌了,南口面对敌人。南坑道口进来有两个拐弯,敌人的机枪可以从坑道口打到第一个拐弯处,经常可以看见打进来的子弹头在石壁上撞击出来的火花。我们的两部电台就架在第二个拐弯处。满坑道的地上重叠堆放着三层每袋200斤重的大米麻袋,既当床又当桌子,我们的电台就架在上面。坑道顶上有一棵水桶粗的树桩,正好可架天线。我们将软天线(倒“L”天线)的一头捆一块石头,甩到树顶上,另外一头天线架在坑道口外,下引线接入,按时与团部指挥台联络通了。战斗打响后,两部电台与团指挥所的电台却失去了联络,我和杜定保各守着一部电台,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不通,急死人了。上下通信全无,前方的消息只有负伤的同志回来才知道。战斗停止后,我们的电台又通了。
第一天晚上没有攻下,第二天白天我们再次发起进攻,一气攻占1089.6高地等四个山头,经反复争夺阵地才稳固下来,缴获的战利品不少。敌人退了,机枪打不过来了,但炮火封锁有增无减,转运伤员和补给的伤亡相当大,我们三天没吃没喝,口干了,嘴唇裂了,嗓子哑了,坑道中有一处滴水,那水像酱油一样,又苦又涩,又少,很久才接半缸子,我们四人只能沾沾嘴皮。坑道内大米、鸡蛋粉、肉罐头、燃料有的是,就是没有水。一天,后方送饭的来了,上来五个人,牺牲了四个,只剩一个人送来一桶水,陈营长说,“除了电台留点水外,其他人都不准留,把水送到阵地上去。”我们用水壶留了大半壶,不忍心再倒了。
攻下1089.6高地的第二天晚上,快半夜了,杜定保和我一人一部电台值班,科长在一旁守候,唐杰先、任建民在边上睡觉。突然我的那部电台的指示灯不亮了,我喊了一声“指示灯不亮了,天线断了。”科长也喊了声,“天线断了”。唐杰先和任建民都惊醒了,唐杰先一步窜出坑道,爬上山头,抓住天线两头,第二发炮弹又来了,唐杰先卧倒在地将天线接好,顺势从坑道上方滚下来。任建民则在坑道口用报纸包下引线,一会又一发炮弹正好打在坑道口上方,任建民同志负伤了,伤了六处,被送到师卫生营,最终因感染破伤风而牺牲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战斗经历。60多年过去了,作为老兵,我为我们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光荣,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和平稳定感到欣慰,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强盛感到自豪。

和平来之不易
感谢每一位负重前行者
谨以此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英雄不朽!